印在心底的联合国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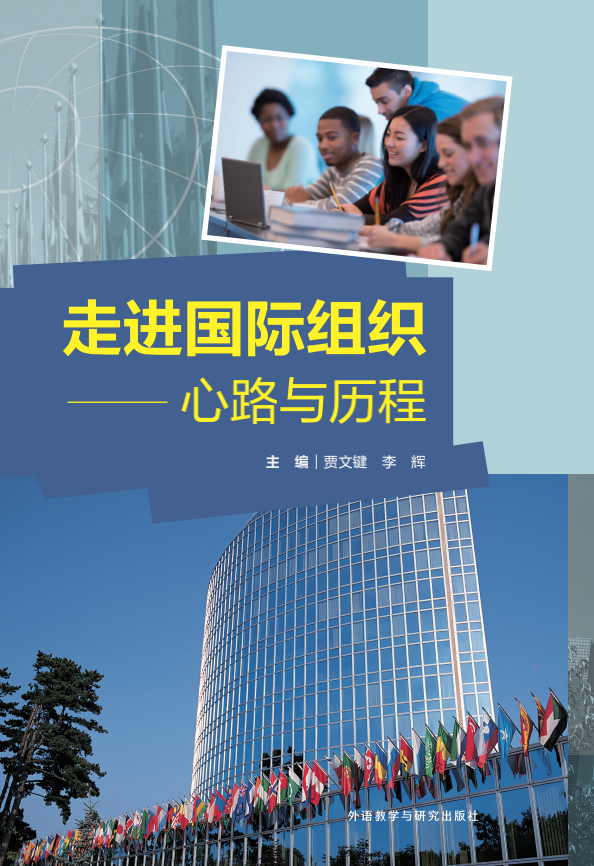
主编:贾文键 | 李辉
十年的成功探索与实践, 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国际组织学院一批又一批同学走进国际组织实习和工作,成长为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为此,学院决定集结同学们在国际组织实习与工作的经历和感悟,编辑出版《走进国际组织——心路与历程》,纪录同学们精彩难忘的工作经历,分享他们多彩斑斓的心路历程,启迪后来的学生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作者简介
About The Author
孔/璐

孔璐,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项目班国际经济与金融方向2019届毕业生,于2018年取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人力资源硕士学位。曾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初级专业官员中心实习,负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合作的实习项目联络工作。回国之后继续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北京办事处实习,现就职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媒体处。

有时候觉得缘分确实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小时候大人们问我长大以后想干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去联合国!”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的玩笑话,如今却成了现实。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也许是从小受到的熏陶,也许是在触碰到些许与联合国有关的事物之后开始暗自努力,才走到了今天,坐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北京办事处实习。两个月之前,我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丹麦总部初级专业官员中心的办公室实习。继续追溯,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项目班和爱丁堡大学忙到一抬头时光就不见的日子。而选择北外国际组织项目班又缘起于本科期间曾参加的各种国内外“模拟联合国”活动。
以上这200多字倒叙了我几年的路程,没有走弯路是值得庆幸的事情。我曾听过朋友的经历:学习或者工作到一半发现并不喜欢也不适合所在行业,但是全身而退的沉没成本太大又不敢轻易改变。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或许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这么说还为时过早,但至少现在,我还很固执且满心欢喜地追求着我的联合国梦。
2018年,我通过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的实习项目申请获得实习机会,岗位地点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之一—哥本哈根,具体实习单位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初级专业官员中心。该中心为人力资源局的分支机构,负责联合国系统内17个机构的初级专业官员项目,主要业务包括伙伴关系的建立与业务开展,岗位宣传,候选人筛选、聘用和培训,绩效管理及薪酬管理等。除此之外,还负责与部分国家政府签署实习生项目合作协议。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式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实习生项目合作协议,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国家留学基金委每年将选拔并资助至少10名中国实习生到开发计划署相关岗位实习。
我申请的岗位负责2019年即第二届合作实习项目的全程协调工作,主要包括该项目的前期信息发布与宣传、申请人的岗位意向收集、与用人单位的协调与沟通、协助用人单位进行最后筛选与定岗等。除此之外,还要协助初级专业官员中心的选拔工作及团队运行所需的其他工作。
相信很多人都对申请实习的过程感兴趣,我就先来讲一讲我的经历。我是通过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的渠道申请获取本次实习机会的,由于联合国系统内的实习生通常没有报酬,所以能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我深感幸运。当然,国内选拔竞争激烈,我在申请过程中也承受了不少压力。整个申请周期较长,历时五个月,我于2018年4月提交了申请材料,5月完成笔试,6月接受第一轮面试考核,到8月才收到第二轮面试通知,9月正式收到录用通知。这期间正是我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最后一学期,面临着考试与毕业论文的双重压力,但在老师与朋友的支持帮助下,我顺利地安排好各个申请阶段的事宜,每一考核阶段都为自己预留了充足的准备时间,以较好的状态投入考核,最终被录取。
要谈申请实习的经验,首先是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保持良好的心态。既然选择了以国际组织为最终目的地的职业生涯,就要考虑到相关情况下的取舍,例如舍弃应届生身份和家人的陪伴,选择海外独立生活与文化交流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冲突等。其次要做好充分的应试准备,并在面试中展示出来。仔细研读岗位描述,对所申请的岗位及办公室背景有所了解,在与面试官的对话中充分展现个人经验和技能与岗位的匹配程度。但以最终面试结果来看,相较于联合国系统的正式员工,用人单位对实习生的要求和期许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毕竟实习生经验不足是常态,他们更看重的是工作动机、性格品质、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可塑性。

2018年11月17日,我登上了前往哥本哈根的飞机,带着对工作单位的憧憬去报到。因为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我当时匆匆在网上预订了一间短租房,一个月的房租就花掉了一半的补助。到达之后我放下行李,准备出门透透气。结果出门右拐就到了游客如织的新港,难怪房租这么高,原来自己住在市中心的中心,转身又发现了已然热闹起来的圣诞集市,忍不住越逛越远,全然忘记了舟车劳顿的疲惫。19日,我开启了联合国实习的第一天。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总部大楼被称为“UNCity”,位于北港边。从空中鸟瞰,这座大楼呈“米”字状,过了安检进入大厅,一个形似八爪鱼的大旋梯将“米”字楼的各个分支联系在一起,员工们把这些分支叫作“finger(s)”。联合国机构有着高标准的安保系统,外来人员除了安检之外,还需要有内部人员的邀请才能进入。一进门,我便看见之前通过邮件联系的同事伊万娜在大厅等我,她很热情地带我去办工作证,然后领着我一边参观一边介绍大楼的情况。接着我又被带到即将实习的办公室,认识了在之后九个月里待我如家人的同事们。我注意到大家对我专程从中国飞过来实习很好奇,即使伊万娜介绍我时没有提,大家也会问,大概对他们来说,有人专程从中国飞到丹麦来实习是少之又少的事情。确实,我是团队中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实习生(或者说中国同事)。后来我才发现,在这栋容纳了2000多人的大楼里,中国人居然只有二三十个,难怪大家对我、对中国那么好奇,总是能抛出一万个为什么。
第一个星期,在茶水间或是走廊碰到同事,每个人都会特别关心地问我生活住宿是否安排妥当了、感觉怎么样,这种关切让我一下子消除了距离感,与大家放开畅谈。丹麦社会极具扁平化特征,哥本哈根联合国总部的工作环境也是如此,从实习生到部门主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也相互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工作。即使是部门主管,大事小情也一律自己动手,除非实在忙不过来,否则不会随便把无关紧要的小事甩手交给实习生。
我的实习导师叫让·吕克,是一位非常可爱、毫无距离感且极具语言天赋的法国人,交付任务时语气总是非常客气,我完成任务后也总会跟我道一声谢谢,每次交谈都会鼓励我抒发己见。我还记得他第一次给我布置任务的时候,话说到一半,突然插进一句:“你如果有问题或想发表意见可以随时打断我,我不是你的上司,我的位置在这里。”说着,他屈膝用手比画着他所说的“这里”有多低。听完这话,我感到莫大的舒心,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满满、能问问题绝不憋着的人。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期间,同学们给我的“荣誉称号”就是“最能问问题的人”。所以这话让我放下了初来乍到的紧张与顾虑,很快就顺利开启了工作。
前两周工作不多,只要求熟悉这里的工作方式和机构体系,随后,新一轮国家基金委和开发计划署联合实习项目开启,我也开始了我的核心工作。起初我将该实习项目简介挂在开发计划署内网上,但是并没有什么反响,可能刚好赶在了圣诞假期,也可能是大家并不太关注内网。后来我们决定给各个区域的人事联络人一一发送邮件推广项目,我也因此在开发计划署的工作网络中建立了最初的结点,从这里出发,我织起了越来越大的网。我们的信息散播非常有效,陆续从世界各地的办公室收到30多封用人请求。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对接以及各个地区办公室的互动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其中有对提交系统不熟悉或不按要求填写岗位需求的,有对后续流程充满疑问的,有提出特殊要求的……我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一一处理。导师教我开启了第一步工作之后就放手让我去做,按我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来工作。偶尔碰到棘手的情况,我会去询问他的意见,他的工作经验使他能够看到我所不及的方面,考虑得更加周全。

我的团队,是待我如亲人的团队,直到今天,我还能回忆起与每个人相处的细节。还记得,实习不到一个月,临近元旦,菲律宾同事莱米怕我一个人跨年太孤单,特意邀请我参加她的“新年趴”,与一群素昧平生的人一起包饺子、做美食,饮酒畅谈、游戏、唱歌,最后一起新年倒计时、赏烟花,因为大家格外照顾,我不曾有一丝陌生感。那一晚我的虾仁炒饭得到了公认的好评,第二天整个办公室的人见了我都说想尝尝我的炒饭。
同样担心我独在他乡会感到孤单的还有英国同事罗莉,每天清晨她都会一一与每位同事打招呼,热情地问一句:“Allwell?”(一切都好吗?)时间一久,闻声便知是罗莉来打招呼了。她对我是格外嘘寒问暖,每当看见我下班时间还留在办公室敲键盘就催我早点回家休息,每当听我描述自己过了一个多么充实的周末或假期时,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大概常年独居在丹麦的她对我能感同身受吧。我十分喜欢她的英式口音,与她的英式幽默搭配起来,极具个人魅力。
自己空降到一个语言与文化环境完全陌生的国度,紧张和惶恐是再自然不过的,两年前我初到苏格兰时也曾下意识地缩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随着一些无法避免的接触,我开始慢慢了解和习惯异质文化,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之处,适应差异并慢慢把差异变成习惯。曾经走在大街上,我会下意识地去分辨每个路人的国籍,不知不觉中,这种习惯消失了,来往行人只是路人甲乙丙丁,是和我一样奔走在欧洲某国某地某条街道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想,当一个人不在潜意识里做文化区分,能不假思索地开口与人谈话,而不是先在心里紧张地梳理语言,大概就已经融入了异质文化。

初到丹麦,其实并没有想象之中“童话王国”的感觉,整个哥本哈根的建筑风格很单一,色调和形状透露着典型的北方民族的粗犷和简朴。但是内饰却极具设计感,从家具到摆件都是很有格调的极简主义风格。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都会忍不住驻足在商店的橱窗外欣赏,心想以后有了自己的小窝一定要装饰成这样,但是看完吊牌价格之后又被一盆冷水泼回现实。丹麦的物价很高,丹麦克朗和人民币大概等值,随便在一家餐厅点一道主菜价格都在140—180克朗之间。为了不把钱花在雷区,我极少在外用餐。丹麦人很喜欢吃猪肉,丹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之一。在丹麦比较出名的一道菜,也是圣诞餐桌上必不可缺的一道菜,就是洋葱苹果烤猪肉,猪肉切成薄片,烤得皮脆肉嫩,配上烤软的苹果和洋葱解腻。丹麦人的饮食结构非常健康,对很多人来说,两片又硬又酸的黑面包,放上一罐腌渍鲱鱼或金枪鱼,再配点蔬菜沙拉,一顿午餐就完成了,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开放型三明治”(opensandwich)。上述只是最简单的做法,市场上还有好多种让人眼花缭乱、食欲大开的开放型三明治,每个的价钱通常是六七十克朗,性价比并不高。而在中国热卖的丹麦曲奇其实没什么特别之处,反倒是黄油曲奇更胜一筹。
转眼已回国九个月了,回想起办公室外那片深蓝的海和海边发生过的故事,以及与海天相映衬的联合国的蓝色旗帜,倍感亲切。虽然没能以正式员工的身份留任,但这份“联合国蓝”已经印刻在我的心底,成为我人生道路的主流色调,引导我砥砺前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感恩自己生长在追梦国际组织的黄金时代,通过国家资助踏进了联合国,离梦想又近了一步。逐梦之路道阻且长,希望有一天再回到那里,我已经是联合国的一员了。

文字:孔璐
编辑:王贤思、王弘书
审核:李爱国


